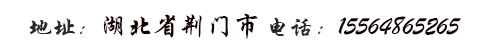山地救援医生极端自然环境下的野外医疗
|
刘云涛 https://m-mip.39.net/nk/mipso_4305593.html 《山地救援医生》极端自然环境下的野外医疗 作者:克里斯托弗·范蒂尔伯格(医生) 请尊重译者!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或摘抄,经授权转载时请不要删去译者姓名,也不要篡改译文,如有指正请私信译者。 译者姓名:孟春;潘笑冰 网名:校长;上兵 第三章:岩鼠队“这是你的生日,你做主,”当我问我的妻子是否可以取消我俩骑行的约定,而去参加另一个救援行动时,她这样说。做山地救援志愿者的另一半是非常困难的。有时,詹尼弗很支持我参加重要的行动,毫无怨言。她给我灌满水瓶还给我装上一包食物,甚至经常会在我回家时准备好晚餐。她得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照看孩子。她支持她的丈夫,间接地支持整个社会。和其他的户外发烧友一样,当有人受伤或失踪,她都很难过。而且她清楚也许有一天,如果她自己也需要救援,就需要象岩鼠队这样的人,和他们的配偶来帮助她。但是救援行为确实在我俩的婚姻中造成一些摩擦。我错过了晚餐派对,我逃避家务,比如没时间给草坪除草。 很久以前我就决定继续为山地救援做义工,即使我们有了孩子后也没改变。我没有和男生们一起出去玩,也没有什么私人旅行,我倾注全部精力照顾女儿们。作为急诊医生的4小时轮班制,每个月工作十天,这给了我比大多数父亲更多的时间陪孩子。我还决定工作再少点,追求一种不要太多钱的生活方式。没人到死还想着应该多干活。但是,结果是,在一年最忙的时候响应征召去救援,是绝不可能得到老婆笑脸的。当我在年初告诉詹尼弗我会加入志援消防部门时,她眉毛上扬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他们怎么样?”她担心那个攀登者。 “不知道,”我说,一边穿衣服一边给佩妮打电话。 “是谁啊?”她问我,希望不是她认识的朋友。 “不知道。” “受伤了吗?” “估计是,但是不确定。” “伤的多重?” “不知道。” 所以在我的生日那天,托德威尔斯和我又开着车颠簸在云幞路上。到冬天会用来封锁道路的那扇门锁着,我们俩绕了过去。留下两位岩鼠队员——伯尼威尔斯和科克沃瑞等着森林管理局的人来开门,到时他们会把我们的卡车和雪地履带车开上来。山路很干燥,辗过的车辙里满是尘土,堵塞了我的空气滤清器,尖利的石头对车胎造成很大的威胁,我好像每年都要在这条路上爆一条胎。在6公里处,一只小熊冲过我们面前的道路,逃进茂密的针叶林;10公里处,像下水道那么粗的一棵道格拉斯冷杉倒在路中间,如果用我车上的折叠锯子,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锯断。我们没法再往前开了,况且,在阳光照不到的北侧,道路上还有几片积雪。 胡德河镇(包括河谷、小镇、同名的河流)是一个荒凉的山区,海拔米,这个地方被夹在南喀斯喀特山脉两座巨大的火山中间,在华盛顿州的胡德山和亚当斯山之间,哥伦比亚河正好流经这里。很多年来,胡德河是一个水果之乡,也是伐木工的卡车驿站,从这里他们把砍伐下来的原木拖出森林。80年代初,冲浪运动爱好者发现了哥伦比亚峡谷,从太平洋过来的海洋冷空气吹向内陆的波特兰,被俄勒冈东部和华盛顿州炙热的沙漠气流抬升,形成了一个公里长,多米高的风带。由于风逆流而上,在河中形成了3米多高的巨浪。几十年来困扰果农的大风,创造了理想的冲浪环境。因此,胡德河成为世界上首选冲浪圣地之一。并且,不单单是由于冲浪运动,随着90年代其他户外运动的流行,胡德河涌入了各种探险者。飞钓的,登山的,山地车骑行的,滑雪的,玩单板的,玩皮划艇的以及其他各种冒险运动的发烧友,这帮人被称为:“肾上腺素瘾君子”。 尽管担心房地产项目会摧毁果园,胡德河还一直保留着一些家庭经营的果园,大多种植西洋梨和冬梨、桃、青苹果和红富士,以及在较温暖和干燥的东部县境,还出产“宾库”和“安妮女王”樱桃。镇中心,曾经充斥着廉价餐馆和冲浪用品商店的地方,后来都转型成大量的小时装店,鞋专卖店,儿童服饰店,玩具店,珠宝店,宠物用品店,冰激凌店,咖啡馆和女装店。周末和假期,人们从波特兰开车一个小时来此购物。 幸运的是,尽管变化巨大,我们小镇仍然保留着乡村田园和山区文化。我们社区的核心精神体现在我们的山地救援历史上,强悍的当地志愿者奉献他们的时间去救助那些处于困境的人的故事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尤其是考虑到岩鼠队是这个国家第一支正式的志愿山地救援组织。 几个世纪以来,志愿者们,就像胡德河那些人一样,一直在世界上最严酷的环境救死扶伤:高山,沙漠,丛林、森林,还有海洋。最早期的救援志愿者是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僧侣,由奥斯塔副主教伯纳德门顿于年创建了这支僧侣救援队。如今,座落于瓦莱阿尔卑斯山脉的彭宁山口的修道院仍在接客,位于意大利和瑞士海拔47米的阿尔卑斯山中。僧侣们最出名的是他们备受尊重的搜救犬。这些罗马莫洛索斯品种狗一开始是用来拉牛奶车,它们有着厚厚的皮毛,温顺的个性,强壮的四肢,敏锐的嗅觉,十分招人喜爱,它们也被叫做修道院犬,后来改成圣伯纳犬。自年以来,它们已经救了多人。奥古斯丁修道士在整个阿尔卑斯山区修建了急救站和山区驿站。最值得奥古斯丁僧侣们自豪的是,年11世教皇尊伯纳德门顿为“攀登者守护神”。 在18世纪晚期,登山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兴旺起来,有组织的山地搜救随之出现。萨沃伊公国准许*职人员组成一个志愿向导和救援服务组织。随后,在年,撒丁国王成立了一个名为“霞慕尼向导联盟”的向导和救援组织,以保护勃朗峰不被破坏。 瑞士阿尔卑斯俱乐部成立于年,执行阿尔卑斯山区的山地搜救任务。瑞士“Parsenndienst”是一个冬季滑雪救援机构,负责把受伤的滑雪者从山上拖下来。年,欧洲的山地救援者联合在一起,成立了“阿尔卑斯救援国际委员会”。 在美国,搜救可以追溯到年,当时为应对海事灾难在东海岸成立了救生机构。年美国的第一家搜救机构成立,这就是“美国海岸警卫队”。当西方世界稳定后,美国人开始把登山作为一项运动。 进入太平洋西北的喀斯喀特山脉,一连串终年积雪的火山从加拿大哥伦比亚省一直延伸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直到0世纪0年代,这些山峰上的救援工作,尤其在华盛顿州的胡德山和雷尼尔山地区,都只依靠为数不多的国家森林服务机构护林员,在一些志愿的攀登者、向导和*人的帮助下进行。但年,在胡德河的一个小山区的社区里,一切发生了改变。 年8月10日,似乎是太平洋西北海岸的一个温暖夏日。天空晴朗,空气温暖宜人,徐徐微风拂过树梢。胡德山顶云雾缭绕,温暖的海洋空气在寒冷积雪的峰顶被雾化成一条晶莹的项链,悬挂在胡德山的脖子上。 11岁的男孩,杰克斯特朗和他哥哥出发去胡德山的“洛斯特小溪”里钓鱼,后来在林线上方的维斯塔山脊迷路了。一连三个晚上,他蜷身在野外,喝溪水,靠找到的野果充饥。县治安员召集了几百个志愿护林员、警察、警员、徒步者,邻居和波特兰第七步兵团的战士来搜救。在搜救过程中,只有胡德河的攀登者具有技术和装备,能上到林线以上永久雪原和冰川。攀登者梅斯鲍德温研究了地图并向男孩的哥哥了解了情况后,大喊:“我知道这孩子在哪里。”8月13日,鲍德温、珀西巴克林和杰西帕迪在林线上方一块突出的岩石上找到了男孩。他在不由自主地哆嗦着。登山队员们燃起一堆火并朝天放了一枪,表示找到男孩了。第二天一早,人们兴高采烈地抱着孩子出了山,媒体问他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岩鼠队的,”鲍德温笑着回答。梅斯记得一个登山者的妻子说过,“这些家伙只是每个周末都爬峭壁的一群老鼠”。这个名字就这样沿袭下来了。 此后不久,志愿的山地救援群体开始在多山的西部风起云涌。6年,在胡德河,查尔斯米诺特多尔开始在胡德山组织滑雪巡护队,帮助蓬勃发展的滑雪业进行事故急救和救援。滑雪巡护队在各个雪场迅速发展,最终成为一个规模达到人,在全国各地有支巡护队的组织。年,多尔受雇培训美*山地搜救和山地作战。由此,美国陆*著名的第十山地师成立,并首次在雷尼尔山进行训练,然后又转到了科罗拉多的黑尔营。美国阿尔卑斯俱乐部成立于年,旨在推广登山技术、科学勘探和自然保护,并在年组织了一个安全委员会。委员会出版发行了“登山安全”手册,分发给登山爱好者。 年6月6日—7日,在胡德山的Timberline旅馆里,西海岸的山地救援志愿者济济一堂,成立了“山地救援协会”。那年定下的两个主要目标至今仍被遵循:提供山地搜救和山地安全教育。 今天,有超过85家单位,逾位志愿者在协会中工作(还有一个针对非山区搜救的姐妹机构——“国家搜救协会”,有14名会员),在全美国每年处理几千起事故。有些救援队每年被召集10来次,另外一些年平均要执行多次任务。救援人员主要由志愿攀登者组成,但一些队伍里也有拿工资的人,比如麦金利、优胜美地和大提顿国家公园的登山巡护员;美国空*伞降救援队,预备警员和精选的消防救援医疗队。随着户外运动越来越普及以及极限运动越来越流行,与山地搜救有关的学科也在不断拓宽。现今,一个救援队有可能被叫去进行沙漠搜救,河里的激流搜救,封闭空间的洞穴救援。多数救援队依靠基金、税收拨款和捐赠。从一开始,救援的核心就是市民们愿意帮助野外受困的人们。 象过去和现在的很多山地救援者一样,“岩鼠队”是一群有家庭且把户外运动当做生活方式的人。我们是果农、木工、教师等。我们有消防志愿者,医护人员,还有一个专业的临床治疗专家。团队里有律师、园艺师以及本县唯一的两位法官。很少有人会有好几天不做跑步、山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双板滑雪、单板滑雪,攀登、皮划艇或徒步运动。把我们维系在一起的基础是对户外运动的热爱,加上对自然的尊重、敬畏,我们深爱着巍峨的大山,宽广的雪原和冰川,险峻的山峰,茂密的森林以及狂野的河流。 每一个加入团队的人都有一样山地绝技:有些人是登山探险的专家,攀冰高手;有些人有基础的冰川攀登知识(入会的唯一要求是登上过胡德山和亚当斯山,且是胡德河县居民)。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具体的、高度专业化、高度集中的目标:进入荒野去搜救迷路或受伤的人。 我们把宝贵的时间、精力和个人资源献给救援队和社区,每年执行15到0次任务且分文不取。一般情况下,一个活跃的会员一年中会有0到40小时救援任务,0到40小时的非救援任务。我们每月要开例会,一年6到8次培训、社会宣传活动、户外旅行。我们还要修理保养装备及我们的两处办公楼。 在一次救援中,不是每个人都要下降到裂缝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一个人在家协调救援工作;一到两个人作为先遣侦察队,第一时间冲到现场去评估情况;一个人负责现场的事故指挥;另一个被派做医护人员。一个人也许会负责开车运送伤员、食物,或者背装备上山。有时候带上山的装备能救命,但有的时候用不上,就要再背下来。有时我们等待指令,等着在需要的时候冲上去,或者在不需要的时候撤下来。偶尔,我们也会什么都没干就开车回家。 与许多志愿者团队不同,除了志愿消防队外,我们是唯一需要4小时备勤的。通常我们对地点、伤员和环境知之甚少。救援也许是和死神赛跑,也可能只是护送别人走出森林。一个“在老鹰溪头部受伤”的紧急救援,可能会转变成“在鲁克尔溪有人崴脚”的闹剧;一个“在麋鹿牧场心脏病发作”的急救,也可能以只找到一个在牛顿溪峡谷里能自行走回去的徒步者收场。 我们丢下工作、家务、晚餐派对、温暖的床,也无法预先通知家人,只有很短的时间准备。 就个人而言,我们有很多理由希望成为山地救援志愿者,这是一种社区服务,我们“积业”(佛家说善有善报),有一天我们也会需要帮助。这种同志情谊与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截然不同:我们因为一个共同的、鲜有人能完成的具体使命聚集在一起,经常在紧张的环境下工作,有着不可预测的障碍,高度专业化,充满危险,巨大的生理考验,令人崩溃的生死任务都是对我们巨大的激励,当我们把从高山、河流、森林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用在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时,我们从救援成功中获得了深深的满足感。我们在冒险中成长——肾上腺在接到征召时激增,直到任务结束才消失。紧张感令人兴奋,危险是充满着诱惑,而个人满足感是快乐的源泉,那是纯粹的愉悦。你看,助人也是有回报的;否则,下一次召唤,你就不愿意起床了。 现在,在岩鼠队成立将近80年后,托德和我驱车行驶在通向“云幞营地”的山路上,它座落在胡德山北面,海拔1多米的鞍部。有时由于救援情况紧急或者情况不确定,我们要尽快上山。今天,我们花了更长的时间。实际上,这个救援电话是昨晚打的,县治安官办公室接到报警,说有人在胡德山北侧失踪,谢里夫乔坐着单翼小飞机上山寻找。当事人帕特和几个朋友正在翻越库珀斯珀山脊的困难路段,这是一个从山的东北角突出来的山脊。山脊的下部巨大而陡峭,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被冰雪覆盖;越往上坡度越陡。在山体与山峰的结合部,一块巨石横亘在海拔多米的地方,攀登线路暴露感很强,非常危险,多米长的线路直通顶峰。就在结合部上方的大石头上,帕特感觉不舒服,可能是急性高山病。 急性高山病也被称做高原反应,AMS是由于低气压和空气中较低的氧含量导致的,可能只是小问题,也可能会严重到威胁生命。人的肺部需要吸入足够的氧气并在足够的气压下穿过肺膜进入血液。在血管里,氧气附着在红细胞内的血红蛋白上,随着血液被输送到身体的各个组织。在高海拔,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低,为了补偿缺氧状况,吸气更深,呼吸速度也加快,心脏跳动得更快以便让血液更快地流经全身;肺部加速吸收氧气并把氧气更快地输送到身体的各个组织。血管扩充,以便让更多的血液流向内脏和肌肉。 所有这一切都会改善身体的氧合作用,但是也有副作用。症状包括头疼,这很可能是由于大脑缺氧,同时血流速度加快引起颅骨内的血管充血;疲劳,头晕,恶心,嗜睡,呼吸困难,发冷和易怒。很难区别AMS和疲劳、晒伤、饥渴,所有这些都会让登山者感觉不适。 AMS可能发生在0多米的低海拔,但是常见于海拔米以上,美国西部的许多滑雪场以及步道和攀登线路,都在这个海拔高度上。在这个高度,高山病可能威胁生命。严重的高反会导致注意力难以集中,行走困难,甚至呕吐。高原肺水肿是由于心脏和肺部超负荷运转,造成体液流入肺部。同样,体液也可能流入大脑,造成脑水肿,这会引起神志不清,说胡话,最终昏迷。 预防是最主要的手段。除了保持状态,充足的营养和补水之外,关键是积极适应。“低处睡,高处爬”是攀登者普遍遵循的理念。爬一座山时,建议逐步上升,特别是当这座山的高度超过3米时。那些业余攀登者和冬季运动爱好者,他们只利用一个周末出来滑雪或攀登的人,是高山病的高危人群。对平时生活在海平面高度,突然飞到西部滑雪场或去登山的人,尤其如此。他们要在一天的时间内去攀登一座山峰,很可能会得高山病。 如果你意识到有轻度的AMS症状,初期最好的治疗就是休息、进食和补水。如果症状没有在几分钟内改善,治疗很简单但极其困难:就是下撤。马上下撤并不总是能实现。山地医生可以使用类固醇,利尿剂等药物缓解症状。对于生命垂危的AMS病人,可以把他们放在高压氧舱里,这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当病人被放进去后,按照海平面高度的气压,加压注入氧气,使更多的氧气进入血液循环。 幸运的是,帕特理智的放弃了冲顶。但是他却遇到了另一个麻烦:他要单独下撤。他的同伴们继续攀登。在爬过整个北壁之后,他们会选择一个更安全更容易的南侧线路下降,他们在蒂姆伯莱恩滑雪场南侧准备了第二辆车。帕特的下撤线路看上去很简单:“走下去,几小时后我就能回到车上了。”那是个温暖、阳光充足的下午,他能看到整个胡德河山谷和亚当斯山,圣海伦斯山,以及雷尼尔山北壁。但是他没带地图和指南针。他没带多余的衣服、食品、水。雪上加霜的是,他没太留意上升和下撤的线路,也没意识到回家的线路是一段不明显的横切(被雪覆盖的山脊并没有明显的路径痕迹),帕特需要从库珀斯珀山脊上找到蒂姆伯莱恩小径,这条小径会把他带到西北公里外,回到云幞。从那里,他可以顺着蒂利简小径往东北走3公里就到他的车了。相反,他沿着库珀斯珀山脊下面的滚落线走,也就是石头落下时受重力作用自然滚动的坠落线。雪很软,他可能在齐膝深的雪里高一脚低一脚的跋涉,搞得自己筋疲力尽。最后,帕特进了茂密的树林,到了山脊尽头,侧面是波拉利溪的两道无法逾越的陡崖。他没有意识到他偏离了道路,直到太阳西沉,退到了地平线下,帕特才意识到他迷路了。随着*昏的来临,他停了下来,在树林中给自己搭设了一个狭小的栖身之所,穿上了他唯一一件备用外套,定量配给了食品和水。他没带手机,只好蜷缩在庇护所里过了一夜。 与此同时,他的攀登伙伴们成功到达了山顶,徒步走到蒂姆伯莱恩,取了他们预先放在那里的第二辆车,再开回北侧。但是他们没去找帕特,也没等他,他们换了车,用手机报警说朋友不见了,把车钥匙留在帕特的车里,扬长而去,回波特兰了。 *昏时,谢里夫乔维普勒从飞机上发现了密林中的帕特。乔有一个30公分长的泡沫瓶和一个直径1米的降落伞。他把一瓶水,一部手机,地图放了进去。把泡沫瓶投下去之后,乔和帕特通了电话,知道他在野外过一夜没问题,然后通知了岩鼠队第二天一早上山。 在我生日这天的一大早,托德和我徒步穿过路肩转弯处脏兮兮,压实的雪堆,到了云幞山的鞍部,然后继续穿过树林走上林线。森林空旷祥和。天气热起来,托德和我脱掉一件衣服并且大口喝水。在树林边缘,我们开始呼喊。一小时后一个家伙从树林里钻了出来,被一个大背包压得步履蹒跚,冲着我们跑过来。 “你是帕特?”托德问。 “是,”他用微弱的声音回答。 “我们是搜救队,你怎么样?” “我没事。我很高兴见到你们,”他说,语速很快。“小伙子,警长昨晚投给我这份地图。我不知道我偏离道路这么远。我很可能会摔下悬崖。”他指给我看地图上乔用红笔标注的“悬崖”,就在他宿营地点下面。一直支撑他挺过夜晚的肾上腺素衰减了,这与我们找到的其他受伤或迷路的人一样,突然放松甚至有可能让他们晕过去。他们饥渴、疲劳。托德和我仔细观察帕特。 “你的朋友走了,”托德说。 “我的车在哪?”帕特问。 “红色的本田?”托德问他 “没错。” “蒂利简,”托德说,意指山下离我们步行两小时的停车场。帕特似乎对朋友抛弃他很失望。 帕特做了正确的决定:返回。许多登山者忽视各种提示他们掉头的警告信号,执迷于登顶而受困。没人愿意在登顶前掉头返回,人们窘于接受现实。或者他们认为:“我为了这个周末准备了几个月,或者想:我状态很好没必要掉头。”对我和托德来说,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出行,不算是医疗救助,也不能称之为搜救。我可能还赶得上我老婆和她朋友骑行“多格溪”山径的活动;我已把自行车和骑行装备放在了卡车上。 托德、帕特和我在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停了下来:云幞客栈,一个建在胡德山北侧海拔米高处的小屋:“岩鼠队之家”。我们坐在木制露台上,看着大山发呆,优哉游哉。等着坐雪地车上来的后援团队,现在他们正在一条叫做“老马车”的山路往上“刨”呢。这条小径的名字来自于年建成的一个提供早餐和住宿的BB客栈。托德打开小屋的门,从溪水引过来的水龙头里接了水。我们喂帕特吃东西,给他喝水,这些象灵丹妙药一样使他瞬间恢复了活力。在我生日这一天,我一边沐浴在高山阳光里,呼吸着纯净、凛冽的高原空气,一边仔细思考山上的时光以及棘手的山地救援工作。 胡德山,世界上最具接近性、最流行的适合攀爬的山峰之一,也见证了许多山难,这座山第一次得名叫韦伊斯特,又叫神灵之子,是年美国土著居民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当威廉姆布朗敦中尉沿哥伦比亚河逆流而上时,又以英国海*少将,萨缪尔胡德的名字为它命名。年,波特兰的登山家威廉姆巴克利、齐腾顿、詹姆斯迪尔多夫、亨利皮托克和鲍威尔首次登上了这座米高的火山山顶。线路靠近波特兰一侧,相对容易,也是迄今世界上最流行的攀登线路,每年逾万人尝试登顶。在年7月18号,美国首个登山探险俱乐部在胡德山顶诞生,并以岩羊的名字命名为马扎马斯。他们的座右铭是:Neisikaklalawasahale,奇努克语是:我们爬的很高。 每年我们会有一到两次在胡德山高处的救援,多是以悲剧收场。有些报告说北侧死亡人数是1人。实际上,库珀斯珀山脊路线臭名昭著,在结合部上面的最后一个绳距,被戏称为“最流行的找死路线”。在这地方,攀登者会结组连在一根绳子上,在一个仰角陡坡之上,是米长暴露感极强的攀登路线。这里被夹在侧面和直壁之间的横切上。这个绳段危险而艰难,如果攀登者滑坠,他们会滑出山顶和艾略特冰川之间米的峭壁。。 胡德山充满教科书式的“登山不可为”。近年来事故不断,比如,一个34岁的独攀者滑坠了米,从库珀斯珀山脊掉到了牛顿克拉克冰川上,落在山上一个极为偏远又危险的地方。两位目击者拨打了,谢里夫乔从单翼小飞机上发现了血肉模糊的尸体躺在冰川上。他召集了岩鼠队和国民卫队的直升机。当国民卫队的医生降到冰川上时,他们宣布攀登者已经死亡。他怎么摔下去的?也许是被一块落石击中?也许是他的冰爪卷刃,因鞋底部积雪,造成冰齿无法有效固定。也许是攀登时走神了,被冰镐或冰爪绊倒了。 攀登者使用的冰镐,是一根1米长的铝制管状工具,它一头是尖的,另一头是鹤嘴和镐。这是一个用于帮助攀登者止坠或作为保护点的工具,这种技术称作滑坠制动。但是也许攀登者没有正确的打镐来稳定他的步伐,也许在他坠落的一刹那,滑速太快或者雪太松软,冰镐固定不住。也可能他失手掉了冰镐。 没有冰镐去确保每一步的安全,最好别攀爬。没有搭档,最好也别爬。尽管如此,攀登者还是会因为忽视了基本预防措施而滑坠。几年前,还有一个胡德河人在库珀斯珀山脊滑坠致死。他倒是有搭档和冰镐,他的搭档在给岩鼠队的信中说,尽管死者是个滑雪高手,但可能并不具备登山技能来确保每一步的登山安全,他可能并没有把冰镐结实的插入雪中。滑坠可能是由于他的自制装备引起的,他在攀登中测试一个新的暖腿套,象跳舞和骑行的人用的那种。他把腿套围在腿上,绑在靴子上面,他的冰爪可能踩到了腿套上,把他绊倒滑坠,他和搭档当时没结组。 在另一起事故中,一对30多岁的年轻夫妇结组攀登,他们早上4;30离开云幞停车场,8;00到达顶峰。因为紫外线的照射,气温升高到了0度以上,早晨还是坚硬的雪地融化变软,雪泥湿滑难行,这很危险,因为在雪泥里冰爪没有摩擦力,而且非常耗体力。每一步都会陷到脚踝或者膝盖,意识到了迅速增加的危险,这对情侣立即从山顶下撤,但是他们没有从更安全的南侧线路走。从山顶向下走了几步,他们就滑倒了,尽管他们连在一根绳子上,但是这个预防措施在攀爬陡峭、裸露的线路时通常不管用,比如库珀斯珀山脊。事实上,和搭档结组可能比无保护攀登还要危险,除非你在线路上设置保护点,把雪锥等固定保护器材埋入雪中,再挂上绳子,这能防止攀登者滑坠。这些保护器材:包括雪锥,雪铲,冰锥。一个攀登者滑坠的力量大得惊人,这个巨大的力会施加在绳子上,攀登者的搭档几乎无法承受。因此,如果没有保护点,他会把另一个攀登者拽倒。这对情侣,在这次为攀登阿拉斯加麦金利峰做准备的训练中,滑坠了多米直到艾略特冰川。 有些人简直是从胡德山山顶掉下去的。一名9岁的攀登者从南侧线路登顶了胡德山。当她和队友拍合影时掉了下去,没人看到她摔下去,但他们猜测她在悬崖边失去了平衡,她也摔落在艾略特冰川上了。 同样,一个0岁的单板滑雪者也是从南侧攀爬,于早上6:30登顶,他原计划从库珀斯珀山脊滑下去,再爬回山顶,然后从南侧下去。他只在库珀斯珀山脊转了一个弯就摔到了艾略特冰川上,掉在了其他人坠落的同一地点。 大约0年前,在我和詹妮弗结婚前的一个月,我第一次和我哥哥皮特攀爬胡德山。我们徒步经过“道格线路”,一条最容易的上升线路,选择了三月份:攀登的安全期。峭壁还结着冰,冰裂缝还没打开,雪冻的很结实,非常适合徒步,天气也很晴朗。我们在晨光熹微时离开蒂姆伯莱恩旅馆,上午10点到达最后一个山脊:霍斯巴克(山体结合部)。我们爬上了最后一条雪槽,这是顶峰下一条狭窄陡峭的冲沟——被戏称为珍珠门,因顶峰的石头被白霜覆盖,在晨光下熠熠发光而得名。我记得当时很害怕,但不是被陡峭的雪坡和岩石峭壁以及冰裂缝而吓到,那些裂缝才0厘米宽。我是担心太多的攀登者——0个人挤在珍珠门雪槽里。 “别停下,”我对皮特喊。“我们要超过所有人。要是有人摔倒就会把我们带下去。” “好的,我在爬呢,”他大叫着回答我,在雪中一路向上攀登。当我们到达峰顶时,我们分享了一小瓶香槟、意大利香肠片、奶酪和法式面包。但是在下降到人多拥挤的地方时,皮特和我都感觉这是危险的地方:攀登者太多,水平和经验参差不齐,沟槽陡峭。 00年5月30日,胡德山遭遇了几年来最严重的山难。许多人之前曾预测它会到来,那些年我也一直担心过。在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攀登线路上,三个独立的团队在最后一个绳距同时攀登,就在登上霍哥贝克山脊,通过珍珠门时,那条路狭窄、陡峭而拥挤。当时是个阳光明媚的温暖日子,气温在零度以上,线路上的许多人产生了虚幻的安全感。 事故起因是一个攀登者滑倒了,开始滑坠。滑坠逐渐加速并失去控制。他的搭档立刻扑倒采取滑坠制动姿势,把冰镐胡乱打入冰坡试图阻止滑坠。紧接着,一个挨着一个,象多米诺骨牌一样,这个绳队的人被一个个从滑坠制动姿势拉起来,随着他滑坠。现在,四个滑坠的攀登者撞进另外两个绳队,更多的攀登者象被击倒的保龄球一样,此时,3个队伍里的9个攀登者中间没有任何保护点来防止滑坠。滑坠制动的效果微乎其微:他们的速度太快了,瞬间被扔进了霍格斯贝克裂缝里,这是冰川上端一个巨大的裂缝。三个人因重击当场死亡,六个人被深埋在了冰雪坟墓里。吉姆彭宁顿,一个当地医生讲述,事故发生在三秒钟内,他和他的儿子、女儿目瞪口呆,尤其是他们还要下降到同一个沟槽里。 救援行动立即展开。波特兰山地搜救队,蒂姆伯莱恩雪场巡逻队,当地救护车野外救护队都乘着雪地车上去营救。直升机也被叫来了。波特兰空*预备役中队派出了一架处于战备状态的HH-60G铺路鹰,同时塞勒姆的国民警卫队第师投入了两架黑鹰直升机参与救援。 救援人员尽快用绳索提升系统把伤员救出裂缝的同时,直升机开始把他们转移下山。在裂缝上执行吊运任务的过程中,重型空*铺路鹰直升机开始下沉,这是由于直升机制造的下旋气流把它自己庞大的身躯吸向地面。很快,巨大的飞机开始失去控制,旋转下坠。机长灵机一动,引爆了钢缆脱离装置,幸好钢缆在地面的一端还没有连接伤者,没有人被飞机拖走。然后,铺路鹰从天上掉下来,重重地砸在冰川上,并滚下了山坡,也把5个机组成员甩到了舱门外。不可思议的是,机组成员一个没死,地面的伤员和营救人员也毫发无伤。 但是局面转变成了两个救援同时进行:攀登者和机组成员,现场有3死11伤,伤者被轻型的黑鹰直升机和雪地车救走,尸体第二天由地面救援人员运出。这座山因攀登事故关停了一周。飞机的残骸由一架双引擎的大型奇努克直升机运走。 胡德山南坡的救援既不是胡德山也不是美国历史上最惨的攀登事故(尽管如此,考虑到损失的一架万美金的铺路鹰,这次山难恐怕是史上最昂贵的。) 早在年,俄勒冈圣公会学校要求学生们参加一次胡德山攀登活动。然而,在年5月1日的蒂姆伯莱恩旅馆,寒冷的温度,厚厚的云层,凛冽的寒风让这糟糕的一天更加难熬。山上高处的气候更差了,预报说一场春季风暴就要来临。就像俄勒冈州报后来在头版报道使用的大标题:“不期而至的风暴”。蒂姆伯莱恩旅馆的工作人员警告攀登者,劝他们不要上去。雷尼尔登山探险俱乐部计划的另一场攀登活动也取消了。这是一家历史悠久,在美国很受尊敬的登山向导服务机构,因为天气,他们取消了攀登。蒂姆伯莱恩旅馆自己的向导也取消了一个攀登活动。所有人都待在旅馆里或下山回家。 但是托马斯格曼,俄勒冈圣公会学校的领队和学校专职教员,非要“拍张很牛的峰顶照”。凌晨三点,这个由7个成人和11个十几岁孩子组成的队伍离开了蒂姆伯莱恩旅馆,就这个春季的攀登来说,这个出发时间有点晚,因为温暖的下午会使山体变热,雪会融化变软,使攀登变得更加危险。他们进展缓慢,出发没多一会儿,个大人和3个孩子撤了回来。但是格曼不顾拉尔夫萨默斯的劝告,他是花钱请的“技术专家”,也是当地向导,执意前行。队伍行进太慢,直到下午3点,他们才到达离顶米的火山口岩石区,。多数登山队在6个小时内就可以到达这里,他们原本应该在中午1;00前把孩子们带到这里。 随着吹来的风雪,气温骤降,攀爬变得越来越危险。到3米的高度,格曼最终放弃。但是时间太晚了,整个团队被困在暴风雪中。大家甚至无法分清天地。他们下山走偏了,跌跌撞撞地下撤到米。最终,天黑后,很多孩子都失温了,他们挖了个雪洞。孩子们冻的哆嗦,哭成一团。他们完全没有水,食品和衣服。 晚上9点,之前放弃攀登回到蒂姆伯莱恩旅馆的学生和教师打电话求助。俄勒冈历史上最大一次搜救展开了。到第二天早上,5月13日,救援人员彻底搜寻失踪人员,但是暴风雪仍在肆虐。早上某个时候,向导萨默斯和学生莫莉舒拉离开雪洞和那些受冻着、哭泣的孩子。在时速96公里的寒风中,能见度不足1米,他们的求援之旅充满危险。两个人掉进了巨大的白河冰川,神奇的是,他们没有摔进冰裂缝,最后停在了胡德山梅多斯滑雪场,距蒂姆伯莱恩旅馆0公里远的地方。 “噢,上帝,我们获救了,”莫莉回忆她看见雪道缆车时惊呼。 “不,”萨默斯说,“我们要等到所有人都获救才能庆祝。”萨默斯将与数百位救援人员继续搜索两天。 5月14日,在米处又找到了三位攀登者:他们严重失温奄奄一息。很明显,他们离开了雪洞,开始下山。直升机把他们送到了波特兰的创伤中心,尽管医生们抢救其中一个病人花了8个小时,他们还是都死了。 5月15日,天气终于转晴,终于找到了位于白河冰川顶部的雪洞。场景非常恐怖:在雪洞里,孩子们的尸体堆在一起,只有两个幸运的活了下来。由于冻伤,其中一个孩子后来双腿截肢。总共9人死亡。 北美只有一次登山事故比俄勒冈圣公会学校的孩子们更惨,那是冰瀑断裂引发的雪崩袭击了好几支队伍,在年6月1日的这次事故中有11人丧生。 我是在胡德山滑雪和攀登活动中成长起来的,现在仍然会花很长时间在山里。但是对山难的回忆是最好的提醒,提醒人们在山里会出什么问题。一个微小的错误就会酿成巨大的灾难。就算你做对了一切事情,厄运还是可能降临在好人身上,登山运动没有绝对安全。 今天,我们找到了帕特,尽管被他的伙伴抛弃了,还不得不在树林里度过一个提心吊胆的夜晚,但他安然无恙。攀登,和其他运动一样,有不同级别的风险。以冲浪为例:如果你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去南加利福尼亚玩玩碎浪,那风险要远远低于挑战夏威夷北海岸或者东海岸的飓风掀起的滔天巨浪。同样的运动,风险大不相同。攀登就是如此:有很多方法可以降低风险。最简单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处境不安全就转身回家。我不愿意置身于危险,特别是当我想到等我的家人时。我热爱户外运动:通过带孩子们体验各种户外运动时,我获得了很多乐趣,露营、游泳、骑车、远足。但是近来,我开始转向风险更小的活动。 现在,坐在云幞客栈的前廊,我得以借这个机会好好回忆一下这忙碌的一年。今早,因为这次救援和我妻子的争吵,以及我对斯凯拉和艾弗瑞的爱。此地,云幞客栈,对我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地方之一,也能让我从忙乱的现实生活中逃离片刻。此时,安静祥和,不过两周后,夏天的旅游旺季就开始了,这里会挤满攀登者和徒步者。 现在,在晚春的阳光下,从我置身的云幞客栈平台上,我惬意的吃着一块花生酱和蜂蜜三明治,和托德谈论着如何修理我们那辆雪地车,被我们岩鼠队充满深情的起名为“收藏家”。我们等着伯尼和科客开着“收藏家”上来接托德、帕特和我下山。 我在脑海里列了个装备清单,来补充我放在这里的装备,然后给吉姆彭宁顿打电话。也许他有兴趣加入“岩鼠队”。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waluaa.com/awlajd/3836.html
- 上一篇文章: 在大自然中的龟,又是吃什么呢
- 下一篇文章: 首都苏瓦南太平洋上的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