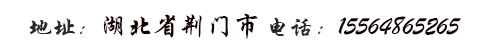小说寻找奥西马斯特2
|
作者 周伟,年出生于南京,现为江苏省作协会员、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家。作品有长、中、短篇小说、电影剧本(已拍摄)、电视剧本、翻译作品等。 第二章:转折点 我独自坐在阿德莱得火车站台上,北上的火车得等到天黑。风从站台尽头吹来,在我的行李旁形成旋涡,使劲朝水泥地里钻。我的箱子比出国时还瘪了些,显然,我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一无所获。奥西·马斯特对我眼下的状况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张名片没派上任何用场,甚至影响了我上学、打工。我不禁自问:继续寻找这个人还值得吗?但北京汉子面如死灰、浑身颤抖的样子又浮现在眼前。他不可能是装出来的呀。 我把行李存了,随便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一直乘到海边。 一下车我就听到了“你无与伦比”。循声望去,这首歌的原唱SinardOconnor从海报上冷冷地注视着我。她的形象我在芭芭拉的CD封套上见过——一个光头的冷艳女子,但海报突出了她忧郁的蓝眼睛,歌声就在她碧蓝的眼睛里载浮载沉。我不知该带着怎样的心态来与她对视:我踏上这片土地就听到这首歌,现在它又跟着我从印度洋到了南太平洋,但半年来的生活告诉我它不一定是好兆,就跟奥西·马斯特的名片一样。 “拷你叽哇!” 我一愣,原来是唱片店的老板学着日本人的姿势朝我鞠躬。“别拷你叽哇,”我说,“我是中国人。” “真的?但你英语说得不错。”那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夸我的英语,而且他显得心悦诚服,“我们把所有的存货都拿出来甩卖,这是你的机会!你是音乐迷,一看就是,对吗?” 其实我算不上音乐迷,不过反正我也没别的地方去。 看到“你无与伦比”的歌词,我傻眼了。这首歌唱的是一个被抛弃的女人对那个男人的思念,而且到了神情恍惚语无伦次的地步,我却一直把这首歌当成精神支柱似的供着。你说她都被人抛弃了还唱那么好听干吗? “好嗓子,不是吗?”老板骄傲地说,好像是他自己唱的似的。 “可是……她的男朋友离开了她!” “那有什么?她会有新男朋友的,我们难道不都想成为她的男朋友?”他憋着笑等我先笑,但我那会儿笑不出来。他只好把笑咽了回去,“你是个严肃的人,旅游者中严肃的人可不多。”我告诉他我不是旅游者,我是学生。“到澳洲来当学生?”他叫了起来,“你开玩笑,澳洲有什么好学的?土著文化?你来澳洲就应该找个海滩躺下来喝啤酒,除此之外,澳洲还有什么?” 我说不出话,因为他说的正是我的感觉。“怎么?你不选几张CD?”他说。我发觉自己已经到了门口,只好说我先到海滩上转转,过一会儿回来买。他叹道:“行、行,不过最好别耽搁太久,我着急找个姑娘一起到海滩上躺着呐!澳洲经济完了!除了啤酒就没有任何生意!我干吗要成天累得像条狗似的就为纳税?” 他的话让我琢磨了很久。我到了澳洲,就像他开了唱片店一样;他没成功,现在准备到海滩上躺着,我呢?我还没取得成天在澳洲海滩上躺着的资格呐! 我忽然扭头朝回赶,唱片店老板老远就咧嘴笑了,“不急、不急,我多着呐!”我气喘吁吁地把奥西·马斯特的名片递过去:“知道这个人吗?” “奥西·马斯特……奥西·马斯特,”他嘀咕着,“好耳熟啊,好像以前有一间办公室叫这个名。” “对!对!在哪儿?” 他摇头,“他们搬走了,我已经长时间没见他们的招牌了。” “可是,他们以前在哪儿?说不定那里有人知道他们的去向呢!” 他眼睛转了半天,“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记性不好——我还以为你是回来买CD的呐。”我只好让他给我拿一盒SinardOconnor的磁带,其实此时我对这首歌已经有点犯怵了,但我对其他歌手一无所知。就这样老板还不太满意:“磁带就磁带吧,聊胜于无,我该高兴才是。谢谢。我建议你到市中心去打听打听,没准有人知道。祝你好运。” 阿德莱得并不繁华,市中心没有奥西·马斯特事务所的招牌。我问了几个人,他们却反过来向我问这问那。我一急英语就结巴,这反倒激发了他们的热情,一时间我身边居然围了五个人。 我终于相信唱片店老板是对的——奥西·马斯特事务所搬走了。起初我有点失望,转念一想,毕竟我得到了奥西·马斯特的消息呀,而且这个人就在我行进路线的前方!我立刻重新被信心注满。步行回火车站的时候,阿德莱得山环水绕的景致多次令我驻足,这无疑也是个适合定居的地方。 正这样想着,一个胖墩墩的女人拦住了我的去路。她说要给我看点东西,然后把我拉向街边的一家理发店。门一开,我差点没叫出来:三个女人没穿上衣,其中两个正在给顾客理发!我惊呆了,眼前只有绕着脑袋旋转的乳房,而且乳房的数量远远大于脑袋的数量。 “欢迎,请这边坐,”第三个无上装女理发师站在我面前,“我给你理好吗?”我当时一定是没控制好自己的眼神,她笑了,“欢迎你看,但不许摸。” “不、不。”我朝后闪,“不理发……我不需要……” “那你为什么进来?” “是她!”我指着胖墩,“你问她!” 胖墩说:“事实上你的头发有点长,我想你该理了。只比一般理发贵一点点!” 我赶紧掏出火车票,“我是该理发了,而且我也喜欢你们的店,但是我得赶火车,真的很抱歉。” 趁她们面面相觑时我想溜,却被女理发师叫住:“你说你喜欢我们的店?你愿意为我们签名吗——我们正在寻求社会的支持?”她拿来签名簿。 “光签名?” “你可以写得更明确一些。” “怎么明确?” “比如:我喜欢无上装理发店。” 我按她说的写了,但写的不太好看。“我再用中文给你们写一遍怎么样?”“那太好了!那样我们就获得了来自全世界的支持。”我于是竖着给她们写了一遍,努力写出*庭坚那种剑拔弩张的味道,并在她们的啧啧赞叹中道别。火车隆隆启动时,我还在琢磨我那样做算不算是助人为乐。后来无上装理发店被曝光,整个澳洲闹得沸沸扬扬,我指着电视屏幕对旁边的人说:“那个店我去过!还为她们题了词!”那些老外都不相信,他们认为我不可能走在新闻的前面。我没有丝毫不快,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摆在了我面前: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并不一定比我多。 总之,数小时阿德莱得的逗留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更重要的是,我离开阿德莱得的感觉和离开佩思时的感觉大不一样,所以直至今日,逢到有人问最喜欢澳洲哪里时我还是这样回答: “南澳。阿德莱得。” 第三章:英语梦话 火车驶入墨尔本阴霾的清晨,我的朋友王志*到车站来接我,没想到他还开了辆旧“斯巴鲁”轿车。“我得抓紧,已经迟到好几次了。”在他一阵手忙脚乱之下,“斯巴鲁”三级跳般地朝滚滚车流冲了过去。我可能叫了一声,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过了多久,王志*的声音从半空飘落:“我还没拿到执照,考了几次都没过。” 王志*原先是个本分人,工作努力却一直没得到提拔。他认为是自己学历太低,于是从83年起就不停地参加自学考试并为此耽误了个人大事。每过一阵子他就义愤填膺地拿个证书给我们看——单位还没提拔他。大家都劝他不要那样苦自己,他嘴上答应说是该歇歇了,但临出国前还是给我们看了一张高级珠算证书。 我在汗流浃背中意识到资本主义改造人比社会主义快得多。他问:“怎么啦你?”“你……非得一只手放在排挡上?”“哦,这样看起来像老驾驶,警察就不会查了。”他把排挡随意晃了晃,车也随之划出了一个大S形,惊起一片喇叭声。我当时估计我身上的汗今生今世也干不透了。 他把我扔给了他的房东又跳跃着起步而去。房东一家三口正在喝汤,确切地说是三点五口——他老婆的肚子已经很显了。房东是公派生,边喝汤边向我介绍他的研究课题,好像是关于啮齿动物繁殖的事。他的研究完全超越了我的经验,我无法理清啮齿动物的繁殖和把老婆带到澳洲来生第二胎之间的关系。听说我外语不太好,公派生拉开架势,大谈特谈他用外语为民族争得脸面的事迹。我想附和却插不上嘴,而他还不停地喝着汤。 “那你,在王志*房间里歇一会儿吧?”他终于说,“掀开塑料布就是。” 王志*居然住在厨房里用塑料布隔出来的地方!他可是自学考试的模范呀!我正在考虑何处下足走进塑料布,公派生说:“你用塑料布把沙发兜进去不就多了一张床吗?等我们喝完汤你把塑料布朝外挪一点,唔……挪两揸吧,那就宽敞多了。”我愣着半天没动,沙发就挨着塑料布,显然是拣来的,要命的是它上面积了一层油腻,此刻正向我发出皮革般柔和的光泽。哧溜哧溜的喝汤声提醒了我:我现在是寄人篱下,必须凑合,何况人家是读博士学位的。我撩开塑料布向公派生道谢,他赶紧把汤咽下,“客气什么?每星期二十一澳元,有一天算一天!” 我惊讶得不能动弹:在厨房公用的沙发上过夜也要三澳元一夜?他即使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啮齿动物繁殖奖,他家厨房沙发也不该这么贵呀! 晚上大家回来了我才知道,这个三居室的小房子里连我在内一共住了九个人。房客中有超时打工者,有至今没找到工作的穷学生,还有两个只想找老外结婚的大龄女青年,他们见缝插针地撒尿、洗手、洗菜、做饭,然后一起拎着锅铲按顺时针方向上去拨弄铁锅里的菜。见我新来,他们七嘴八舌地夸赞公派生承租的房子最能提供安全保障,公派生夫妇任由大家说,脸上的笑绷都绷不住。 等大家都回了房,我问王志*:“你们真的觉得这里好吗?我都有点弄糊涂了。”他朝床上一倒,“其实我们都清楚房租全摊在我们身上了,但我能放心打工,晚上有个地方睡觉,行啦!我知道你心大,你先随便转转吧,如果想走得等到星期天——我只有一天休息。”我一愣,他已翻然入睡。我蜷缩进沙发和塑料布之间,油腻味立刻厚厚地将我包裹起来,不张嘴就吸不到氧气。王志*几乎立刻就开始说梦话了,虽然来澳洲时间与我相当,他却已经养成用中英文交织着说梦话的习惯,有的英文单词他要憋半天,最后以咆哮的方式喊出来。我被吓得抽筋好几次,惊吓之余我得出结论:王志*的英文水平与我不相上下,但口语可能不如我流利。王志*的咆哮持续到后半夜,干清洁工的小伙子忽然从房间里冲出来,在卫生间里咬牙放屁地撒了一泡尿后夺门而去。王志*此刻一跃而起,像是上了发条,匆匆洗漱完走了——他要去送报。我想这下可以睡一会儿了,岂知两个大龄女青年又冒了出来。她们不紧不慢地评价化妆品的功效,然后再讨论早餐的营养搭配。凭心而论她们是体贴入微的,声音一直压得很低,但对女性话题的好奇促使我使劲支楞起耳朵,毕竟我已有半年多没听到这种纯女性的废话了。然后是公派生起来煨汤,他不时去向老婆请示汤里该放什么、什么时候放。 我就那样过了两夜,第二夜和第一夜简直一模一样。 墨尔本比佩思、阿德莱得大多了,而且街上有很多大陆中国人来去匆匆,从“狼”牌或者“火炬”牌旅游鞋上就可以辨认出来,还有牛仔裤——那时候中国的牛仔裤还没与世界接轨,两道边总是砸在裤腿外侧。我暗暗叫苦:奥西·马斯特即便就在这里,好事也轮不到我了呀。第三天临近中午,我坐在街边头晕眼花,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使我觉得这是殖民地时期的上海。我开始为没跟老姚去农场而后悔,进而后悔起当初做出国的决定来了。 我头重脚轻地回到住所,公派生一家又在厨房喝汤!我和衣倒向沙发,塑料布被我震得乱晃。公派生叫了起来:“嗳、嗳、嗳!我们这里正喝汤呐!你轻点行不行?” 我实在忍无可忍,“我在我的卧室里,和你们喝汤有什么关系?” “嗬?我说,我看你是王志*的朋友才让你留下的,你这样说话可有点不给面子呀。” “你没给王志*面子,你给了澳元面子。” “你?!你来投靠别人,竟说这样的话!不乐意就请便,这里可没有户口制度!” “投靠朋友并不丢人,用国家的钱到这里来当超生游击队才丢人呐!” 我摔门出来后才意识到我把话说过头了。看来我不能在这里等到星期天,但我起码得和王志*话别,就是说我得转悠到天黑,可我去哪儿呢? 隔壁工厂正在休息,一个洋妞在门口眼巴巴地看我点烟。我习惯性地问:“你们这里需要人手吗?” 她犹豫了一下说:“可能,但老板现在不在。”她要我留下电话,我从她的眼神判断她准备开口要烟,赶紧说我就在隔壁,一会儿再来。她的目光跟我走了一段,我没回头但能感觉到。澳洲到处有人要烟,他们都和玛格丽特的态度一样:香烟那么贵,我干吗要买?但他们显然不喜欢这个问题的另一半:香烟那么贵,我干吗要抽? 我站在街边抽烟,街对面的职业介绍所冷冷清清。挨家挨户找工作是我们自费生最常用的方式,职业介绍所手续太正规,而且他们练就了辨别中国自费生的火眼金睛。我抽完最后一口,决定去给澳洲劳动就业部添点乱,出口恶气。 架子上的卡片基本上都是旧的,这与佩思的情形一样。它们大多是些远洋船长、坦克设计师、心脏外科专家之类的职务。我估计能接这些职务的人不会到这里来看卡片,因而这些卡片的作用就是提醒一般人:你虚度了青春!当然它们也是澳洲劳动就业部的公告:我们可没闲着! 一张簇新的卡片引起了我的注意。对照小字典,我读懂了这是招一个酒吧服务员,要求是穿很“节俭”的衣服。我回想了好一会儿,确信自己今生从来没奢华过,于是摘下卡片对服务台里的工作人员说:“这份工作我要了,请开单。” 那个外国女同志愣在那里不动,我不想让她有时间琢磨出我的学生身份,大声质问道:“你不认为我很节俭吗?” “但我并不认为你合适这个工作。” “没人会比我更合适。请开单。” “看来,”她说,“只有让他们向你解释了。” 酒店就在街口,接待我的人头发又黑又长,好一会儿我才确信他是男的。他半晌不说话,我看出他不想把这份工作给我,但我不能像对职业介绍所的人那样对他。我说:“我符合你们的条件,而且我有工作经验,你可以打电话去佩思核实。” “你知道我们要招什么样的人吗?” 我以问作答:“难道你认为我穿得还不够节俭?” 他拦住我的话头,“来,我让你看看‘节俭’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他把我带到一扇小窗面前,闪开身子,“你自己看吧。” 一个比基尼女郎侧面对着我。几个酒*突出的眼球拼命朝她胸罩里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节俭。”长头发男人憋了一会儿,忽然笑喷了,“你的误解是我所经历的最有趣的事,哈哈,哈哈,对不起,”他不停地笑,又不停地道歉,“我是值班经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让你填一张申请表,让老板做决定。哈哈,对不起,哈哈,太有意思了。” 我在表格上留下了公派生的地址电话,犹豫片刻,签了一个英文名字:韦恩。当时并没多想,只是不愿再为“周”该怎么发音而多费口舌。 “什么都试试吧,你这样做其实是对的。”值班经理在分手时终于绷出一脸真诚。我却在转身之后哑然失笑:中国的节俭是没好衣服穿,他们的节俭是有衣服不穿,整个倒过来了! 快到公派生家的时候我发觉离天黑还得一会儿,刚要转身,却见隔壁工厂里的那个洋妞指着我向一个秃头汉子说着什么。我走过去:“你是老板?我叫韦恩,刚才来过。” “你说你也住在隔壁?”这是他的第一句话,“你们房子里到底住了多少人?三十?” 我尴尬地说我刚来,正在找地方搬。 “你也在读博士学位?”得知我还在学语言,他立刻又问:“‘圣诞节’和‘岛屿’怎么发音?” 我说:“‘圣诞节’,‘岛屿’。” “对呀!你的英语比那个博士好多了!知道吗,他把‘圣诞节’里的t和‘岛屿’里的s都发了音!如果我的中文只有他这个水平,我是不会到中国去读博士的!” “我也不会!”我立刻响应,我还想说“丢人现眼”但不知英文该怎么说。 “其实我很喜欢中国,特别是一个叫做赛奇湾的地方,你去过吗?” “赛奇湾?”我在心里把叫“湾”的地方过了一遍,“你是说台湾?渤海湾?或者南泥湾,你听过那首歌?” 他一个劲地摇头。“赛奇湾!就挨着北京!一个小村庄,全村人都吃辣子。看,是这样拼的。” 我横竖看了半天,终于认出他写的是汉语拼音。“四川!不是赛奇湾!也不是一个村庄,是一个省,比维多利亚省还大!离北京远着呐!” 他瞪了我好一会儿。“你的发音也有问题。你们中国人发音都有问题,不过你的情况好些。” 我哭笑不得。“那,你为什么喜欢赛奇湾?喜欢吃辣子?” “不、不!我只想去看看他们怎么吃辣子。” 我和他就赛奇湾、辣子展开讨论,并把话题延伸到辣椒的发源地墨西哥。我们的结论是:辣子对人体的作用我们都不清楚,吃不吃辣子属于基本人权问题,但辣子可能与人口出生率有关,因为凡是吃辣子的地方都人口爆满,科学家应该对此做进一步研究。然后我大大咧咧地问:“那么,我在这里工作的事怎么说?” 他的脸立刻沉下了。“显然你是个有意思的家伙,但澳洲经济很不景气,你知道的对吗?工作不是度假,绝对不是。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是不是?” 我点头,其实我很想长叹一声。 “你,下星期一开始吧。”他伸出手来,“保罗·帕契尼,很高兴认识你。” 我为王志*准备晚饭,还买了一瓶葡萄酒。公派生来厨房转了几次,欲言又止——葡萄酒把他给镇住了。 王志*一回来我就问他有没有开瓶工具。他张着嘴愣在那里,我问了几遍他才说:“啊?什么?” “喝酒呀!”我说,“首先得把酒瓶打开——我决定走了!” 他们一下子都冒了出来,但还没来得及提问电话就响了。“我来接。”公派生摆出房东的架势,“喂?哈罗!……谁?韦……?没……没有这个人……” “是我的!”我冲过去抓过电话,“Hello,Waynespeaking。” 是酒店打来的。一个女的向我道歉,并说如果我不介意,她可以为我安排另一个岗位,“今晚你能开始工作吗?” “现在?当然,我马上就到!” 我放下电话,他们都瞪着我。“这是三天的房租,”我数了九澳元给公派生,“连今晚在内。还有其他费用吗,水电煤气什么的?” 王志*叫道:“嗳,你不是找到工作了吗?” “是的,葡萄酒就是为我找到工作买的,但我得搬。你这儿到底有没有开瓶器?我下班回来喝。” 我赶到酒店,值班经理向员工们使了个眼神,他们一齐抿嘴笑了,看来我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女老板伊莎贝拉和她丈夫罗伯特在办公室见我,她只说了一句“有时我也觉得英语是一种很讨厌的语言,真的。”然后就和她丈夫捂着嘴嘿嘿笑了起来。 工作和比尔那里一样,工资也一样。收工的时候我请伊莎贝拉给我开个租房用的工作证明,她犹豫了一下才拿起笔,“你第一天在这里工作……不过,从你对‘节俭’一词的误解,我确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回到住处已是半夜,葡萄酒原封未动。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软木塞捅下去,然后叫醒王志*。他硬撑着陪我喝了几口,说好如果我找的房子不贵并且有地方停车他就和我一起搬。 从与珍妮吻别到在另一个学校注册,我在其中有一个月的时间,到那天为止还不足两星期。看来我的债务问题不要半年也能解决。老姚啊,你在农场没人说话,而且你的味精被我扔进了车上的垃圾箱,真对不住! 王志*猛地咆哮出英语梦话,我在昏暗中笑得浑身温暖。 星期一我去工厂上班,厂门还没开。公派生正巧从家里出来,见到我一愣。“你……什么东西忘这儿了?” “没有。” “那你……?” 我不说话。所有自费生都明白不该把自己打工的情况透露给同胞,尤其是闹过矛盾的人。偏偏这时保罗·帕契尼开着他那辆大福特来了,“很好,韦恩,很好。第一天上班就第一个到,我很满意。”他下车和公派生打招呼,“最近怎么样?我一直认为你的房屋租赁生意是墨尔本地区——可能在整个澳洲是最好的。……怎么说呢,你和韦恩是朋友,而且你先在我这儿申请了工作,说起来有点尴尬,但我必须聘用能够用英语和我交流的人。真的很遗憾。韦恩,进来吧,我向你解释一下我们的工作。” 进了工厂我回头,公派生还在那儿傻站着。晚上我和王志*说起这件事,我们不约而同地担心起来:他要是去举报我们超时打工呢? 两个大龄女青年来看我们,立刻要求搬来同住。她们的一句话化解了我们的担心:公派生赚取房租已不止两年,他不但没向澳洲*府纳税,还拿发票回国内报销,我们从国内国际两方面都可以收拾他。 我感到了另一种恐怖:中国人都是窝里斗的高手,可能连我自己也是。 我们能安全吗?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看来还得找到奥西·马斯特。 第四章:姓名学与乌鸦的叫法 工厂是生产文具的,也就是国内乡镇企业的水平。我最初在厂门口见到的那个洋妞叫丽茜·约翰。我以前一直以为约翰只是名,但在她身上就是姓。她还骄傲地告诉我:她有个哥哥就叫约翰·约翰。 我与公派生发生争执的那天下午,丽茜的确是打算向我要烟的。我当然没有向她核实,不过两个星期过后我对她的财*状况已了如指掌:周一、周二她既有香烟又有午饭;周三她只有香烟没有午饭;周四、周五她一切全无——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是周四,问题再清楚不过了。我上班后的第一个星期四,上午刚休息丽茜就坐到了我身边:“知道吗?我有中国血统呢。” “哦?从你父亲那边还是从你母亲那边来的?” “我母亲的奶奶有十六分之一中国血统。” 我那时候的英语反应还不够快,“别忙、别忙,就是说你母亲的奶奶也还不是中国人?” “当然不是。她只有一点点中国血统。” 我算是有点明白了,“那,到你还有多少?” “嘿嘿,剩下的确不多……能给我一支烟吗?” 我给了她烟,并对她母亲的奶奶的先祖与中国人通婚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她解释说她家来自库克群岛,热带人那方面比较随便,她的先祖未必和中国人结婚,没准只是在海边见过一面就有了身孕。我正推算那是否能与郑和航海的时间相吻合,她又要了第二支。 但我对一个重大历史问题的兴趣却被她勾起来了:郑和自己是太监,可他手下的人是如何解决性的需求的呢?我终于发现丽茜与郑和沾不上边,即使我充分考虑热带人发育早的事实,把她们的生育年龄定在从十二岁到四十八岁,时间还是对不上,再说郑和的船队好像也没朝波利尼西亚方向去过——为了抽烟,丽茜编造了她祖奶奶与中国古代水手在海滩上交媾的历史疑案! 不过她是个十九岁的女孩,问题自当别论了。周五休息的时候,我主动递给她一支烟。她很感动,也有点尴尬,“哦,谢谢,尽管我知道抽烟对身体有害……”说着她一口抽掉了小半截。 库克群岛属于新西兰。丽茜一家先从岛上迁到奥克兰,为了就业又先后到了澳洲。她在家里最小,却是全家工作最稳定的一个,家庭其他成员都靠*府救济金过活,每过一阵子就有人因为长期不工作而被取消救济资格。我问她如果加入澳洲国籍情况是否会好些。“什么?”她嚷嚷起来,“澳洲国籍?我们现在还后悔当初加入新西兰国籍呢!以前我们岛上没有国籍不也挺好吗?” 老板保罗·帕契尼插嘴道:“岛上没有失业金!” “岛上有面包树!” “对呀、对呀。面包树还在岛上,可你们都离开了!” “那时候我还小!我迟早要回去的。” “很好!没准我会抽空去呆上一个星期。一星期足够了吧?面包果吃多了肯定拉不出屎来。” 哄笑声中丽茜愤愤地说:“你是意大利公民,不也一直呆在澳洲吗?” “我的情况不一样!澳洲永久居住权使我不必回意大利服兵役。我不喜欢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我不喜欢,美国如果打伊拉克我也不喜欢。”保罗·帕契尼转向我,“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赛奇湾吗?” “四川!请注意你的发音:四——川——” 他挥手打断我:“战争是人的本能,赛奇湾的人喜欢吃辣子,事实上每一次吃辣子都是对自身的战争,否则他们为什么要出汗呢?我相信吃辣子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好办法——他们不需要自身以外的战争了。” 他推导的方式令我惊讶,而更令我深思的是他们对澳洲国籍的态度——资本家和雇员竟如此一致。 除丽茜·约翰外,工厂里还有一个令我困惑的人名:山姆·朱可夫。山姆可以理解为美国,而朱可夫则是苏联最伟大的*事家,世界上最强烈对立的两种势力同时出现在一个地区,其结果必定是鸡飞狗跳,但在山姆·朱可夫身上显示的却是对立的另一面:冷。 山姆是工头,老板在的时候他几乎不说话,即使在我们热烈地讨论中国血统或澳洲国籍问题时,他也只是在一旁冷眼观看。 由于我、老板以及丽茜本质上都是大白乎,所以没几天我们就混熟了。第二个星期四休息时,我赶紧到大门外的长椅上坐好,带着笑脸回望跟踪而来的丽茜。山姆忽然叫住了她:“丽茜,你有烟吗?” “我……”丽茜很尴尬,忽然说,“你不抽烟的,要烟干吗?” “我有。你抽吧。”山姆居然掏出一盒蓝壳温费尔德香烟。 “多么令人惊讶!太谢谢了!”丽茜兴奋得脸都红了,接过烟匆匆朝我这边走,我却看到山姆的眼睛暗了下去。那天老板不在,山姆一直在不远处绷着脸。作为正在和女人套近乎的男人,我立刻觉出了其中的意味。为了缓和气氛,我把对他姓名的想法说了出来。他瞪着我不说话,我赶紧解释:“我开玩笑呢!”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而且你和我开玩笑不合适。” 我愣住了,暗暗地骂自己没眼力劲。岂知休息时间刚结束,山姆就隔着机器冲着我叫:“喂,到这儿来!喂!你听到没有?” 我有点不知所措,半天才说:“你不知道我的名字?” “我知道,但我认为你不该叫韦恩。” 他们都看着我,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憋不过气来。他又说:“你把这几个箱子放到架子上去,它们碍事。” 他是找茬来了!我说:“要放你自己放,梯子超过了一米四!还有,我叫韦恩和你叫山姆一样,没他妈的任何意义。” “你说什么?!”他叫了起来。他们赶紧拦住他,丽茜的脸都吓白了。 说实在的,他的块头比我大,但我知道这会儿要是软了就得永远受气,我才得到这份工作呢。“不要挑起战争!”我说,那时候我从电视上学到的尽是战争词汇,“你想和澳洲法律作战吗?” “这些箱子碍我的事!” “那你就自己搬!” “中国人,你不知道这里谁是工头?” 我把手中的活一摔,“知道我以前干什么的吗?你这样的都没资格和我在一起工作!你我都是来挣钱的,但你挑起了战争!” “那又怎么样?” “我们之中必须有一个离开。” “你知道了?” “我当然知道,因为你要离开!” 他们都惊呆了。我回到高频焊接机旁,心里却没有一点底。我承认那是我这辈子说的最没谱的话,但我必须镇住他。丽茜在我旁边操作,几次想说什么,我却没给她开口机会。我在琢磨回头怎么向老板解释,毕竟这不是赛奇湾的话题。 老板回来了,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他似乎有点闷闷不乐,什么都没说就进了办公室。许久,他伸出头来:“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发生了什么事?” 我屏住呼吸,只要山姆报告我立刻就去解释,且不管我能表达得怎么样,反正不能由着他一人说。 终于传来山姆低低的声音:“一切正常。” 我听到自己的心脏落回胸腔发出巨响,丽茜也猛地扭过头来。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个好兆,于是我朝她认真地点头。 和工厂相比,餐馆的工作还有点乐趣:隔着小窗就是比基尼小姐,还有成片血脉贲张的脸。这个餐馆和佩思的那个不同,客人去那个餐厅为吃饭,而客人到这里来为喝酒。罗伯特和伊莎贝拉夫妇不时转到厨房里来,他们不是来看厨师斯蒂夫和我工作,而是从小窗里观察酒吧里的酒徒。如果他们一个个滔滔不绝只顾说话,老板夫妇就赶紧让我们准备“白送”——烤薯片上撒很多盐和辣椒面,一盘盘从小窗里递出去。在我撒盐和辣椒面的时候,老板夫妇一个劲催:“再放、再放,那样他们才会多喝酒!” 送回来的盘子里总是只剩厚厚的盐和辣椒面。我观察了他们享用“白送”的情形:指尖捏着烤薯片在盘边上磕掉盐和辣椒面,然后“喀嚓”一声扔进嘴里,连啤酒都没喝一口又去捏第二片。 老板夫妇激烈地讨论了好几次,决定为“白送”增加一味配料:粉状奶酪,然后把盘子放到微波炉里去加温,熔化的奶酪就把盐和辣椒面与烤薯片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令人吃惊的是“白送”被消灭了而啤酒的销售并没有明显的上升。后来我琢磨出了其中的道道:“白送”是在酒的销量下降时才白送的,那时酒*们的肚子已经被啤酒填满,比基尼小姐也被看了个够,因而一体化的“白送”只是为他们乏味的嘴巴增加了一点味道而已。我把情况分析给老板夫妇听,他们将信将疑地叫斯蒂夫停止“白送”。岂知九点半过后,那些酒*们拍打着吧台齐声高呼“白送、白送”,伊莎贝拉出去问他们要什么样的“白送”,他们大叫:“随便你们怎么弄我们都能对付!”看来他们从来都是明白人。 从此“白送”的规矩改为:听到他们齐声高呼我们再准备,不用向老板夫妇请示,也不计较采用哪种配方。于是在一般的日子里,斯蒂夫和我说的最多就是:“今天我们吃什么?” 斯蒂夫的厨艺极其一般,却好显摆。“我在以前工作的餐厅里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宴会,猜猜有多少客人!”他总是这样说,因而我也得一次次地接茬:“多少?” “四十几位呢,吃完了他们轮流过来与我握手!”但他最初说的是二十几位,显然这个数字很快将突破五十。“只要你仔细观察我做菜,总有一天你会成为好厨师的。你看上去不笨!” 我只好谢他,但仍然自己做着吃。他经常拿着叉子凑过来,吃得眼睛直眨。“唔!你有长进了,我说过你会成为好厨师的!这份归我了,你自己再做一份吧。” 有时比基尼小姐收拾了吧台上的盘子进来,嗲溜溜地说:“斯蒂夫,有什么吃的吗?我有点冷呢!” “你觉得冷?”斯蒂夫猛地趴在不锈钢桌子上,“来,像这样趴下,我从后面进,我们就都热乎了!”说罢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任比基尼小姐掐了几下又抓走一把薯条之类的吃食。“韦恩,我敢肯定你也喜欢从后面进——双手都有事情做了。” 我毕竟磨不开,“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一个女孩说话……她很尴尬呢!” “尴尬?韦恩,醒醒吧,你现在是在澳洲!” “澳洲怎么啦?” “中国有乌鸦吗?” “乌鸦?!有呀。” “中国乌鸦怎么叫?” “呱、呱、呱。” “什么意思?” “没有意思,就是乌鸦叫。” “你听过澳洲乌鸦叫吗?” “当然,到处都是。” “它们怎么叫?” “呱、呱、呱。” “不!它们这样叫:法——克、法——克、法——连乌鸦都在催我们呢!” 我笑喷了。他说:“怎么啦?你们中国没有‘法克’这个词?” 我说:“我们说操。” “操?什么意思?” “操就是法克。” “哦?”他愣了一下,“可是‘操’听上去不如‘法克’使得上劲。” 文具厂的生意遇到了竞争。那是个*府采购项目,要货的是澳大利亚空*某基地。保罗·帕契尼已经与空*合作多年,这次报价也与竞争者的基本相同,但这个基地离我们的竞争者很近,运输费的差异使决策者犹豫不决。保罗·帕契尼急得团团转,我们都听见他自言自语的诅咒。 那天他出去后电话响了。山姆在厂房的尽头半天没反应,我估计他是故意的。我没好气地抓起电话,却是一个柔美的女声问保罗·帕契尼先生在不在。我立刻想起了在课堂上学到的全部电话礼仪,把简单的句子弄得长长的回答了她。电话是从空*基地打来的,对方是*需部的采购官员。老板给她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找到她,她想解释一下以免误解。“你能为我转告吗?”“当然。你的姓名?”听说她叫安琪拉·福克斯,我笑了。 “怎么啦?” “没什么。请原谅,我觉得你的姓名把天使和狐狸放在一道很有意思。”(注:安琪拉·福克斯的名与“天使”相近,姓则与“狐狸”为同一词。) “你研究姓名?!”她在那头声音一下子高了,“我的名字还意味什么?” “意味着你美丽、善良而且绝顶聪明呀!顺便问一下,你是什么*衔?” “我的*衔可不高。”她有点沮丧。 “放心吧,”我憋出浑厚的嗓音,“以你的名字和美妙的嗓音,你会得到提升的,很快。”等她咯咯笑完后我又说我们已经与空*合作多年,你们的订单对一个小企业来说无比重要,请理解保罗·帕契尼先生的焦急,但他只想与你们合作下去。安琪拉·福克斯犹豫了,然后答应一定认真考虑。 老板回来见到条子,大叫一声:“韦恩,怎么是你接的电话?!”我还没想好怎么解释,他已经气急败坏地拨号了。他在电话上谈了很久,办公室里终于传出他的叫声:“山姆,到我办公室来!韦恩,请你也过来一下!” “为什么不是你接的电话?”他劈头就问山姆,“你怎么解释?”山姆说他在最里头干活,而韦恩就在电话附近。“可我付了你不同的钱!在我离开的时候你该负责这里的一切!看来我认错了人。”然后老板转向我,“你的英语似乎比我估计要好些,以后我不在的时候由你接电话。山姆,明白了吗?你先去吧。” 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这是要给我加工资呀! “韦恩,空*的订单到手了,你的确有功劳。”老板只笑了一下,“可是,你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姓名的?知道吗,在正规商务交往中使用这种东方巫术很令人尴尬,我警告你今后决不能再这样做!” 加工资的事他连一个字都没提!晚上我在餐馆对斯蒂夫说:“你说的对,你们这儿到处是乌鸦,你们的乌鸦又那样叫,所以你们这儿太法克了。” 斯蒂夫直眨眼:“你的英语很有问题,韦恩。你不可以说这里太法克,没这种说法!” “那我该怎么说?” “你对什么不满就法克什么,当然你对谁极度喜爱也可以法克她。” “我对整个澳洲不满!” “那你就法克澳大利亚!”他扇动手臂做飞翔状,“法——克、法——克、法——” 我的气憋了几天,老板也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转了几天,然后他忽然不知去向了。山姆不知我们该干什么,给老板家打电话又没人接。他把他们聚在一起小声嘀咕,眼睛还不时朝我瞄。他的眼神令我恼火。工资没加着,还有敌视的白眼!不行,我必须改变这种局面。 办公室墙上挂着订单,我给自己安排了活。丽茜过来问:“是老板让你干这个的吗?” “不是。不过,你最好呆在这里为我装箱。” “你怎么知道要干这个?连山姆都不知道呢。” “别问那么多。你到底愿不愿意给我打下手?” 她不再问了,一声不吭地帮我装箱。许久,她低声说:“韦恩,我知道你会赢的,但你以后不要对我太严厉,行吗?” 我一愣,一阵狂喜立刻攫住了我。“行!谁叫你有中国血统呢?” 老板是去空*基地了,途中在加油站打来电话问大家在干什么。我如实报告,他立刻叫山姆听电话。我们都听到了老板在数百公里外的咆哮。然后老板又问我为什么选这份活干,我说你的工厂很简单,日程全都挂在墙上,看订单安排生产,还有比这更容易的吗?“韦恩,听我说,韦恩,我知道委屈你了。等我回来一切都将改变,我保证。”他的话语伴随着引擎轰鸣传来,使我有了一种火线被提拔的感觉。那天下午丽茜光是为我装箱都跟不上趟,“你慢点韦恩,我知道你憋着气,但我没做什么错事!”我笑了,她却更加糊涂,“你,到底是生气还是高兴?” 第二天我独自享用热腾腾的午餐时(那天又是周五)老板回来了。山姆被叫进办公室,他们立刻嚷嚷起来。我忽然发觉自己的英语水平大有长进——在看不到他们的时候居然听懂了他们说的每一个词。他们的嗓门越来越大,再加上丽茜在门口等我的烟,真可惜了我那天的宫保鸡丁。 丽茜接过香烟时神色惊恐——保罗·帕契尼正在咆哮:“我原来只想责备你几句并在公司内做一些调整,但你却连基本的事实都不肯承认,山姆,我不得不说……” “等一等,”山姆·朱可夫在最后时刻有了绅士派头,“我辞了。” 那时距他找我茬只有三个星期零一天。他出门的架势把停车场上的乌鸦惊起,聒噪着飞到铁栅栏顶上。这回我可听清楚了,它们叫的就是:“法——克、法——克、法——” “你怎么啦?”丽茜忽然问。 我使劲憋住笑:“问你自己怎么啦,到现在还没把烟点上?”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waluaa.com/awlacy/696.html
- 上一篇文章: 科学家解释诺丽为什么神奇
- 下一篇文章: 讲座摘要陶立夏爱是最漫长的旅程